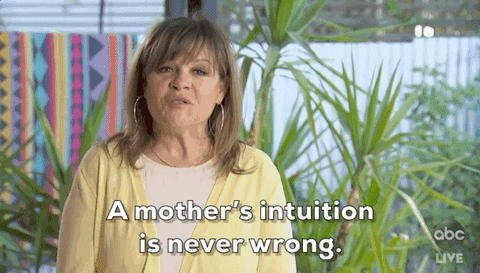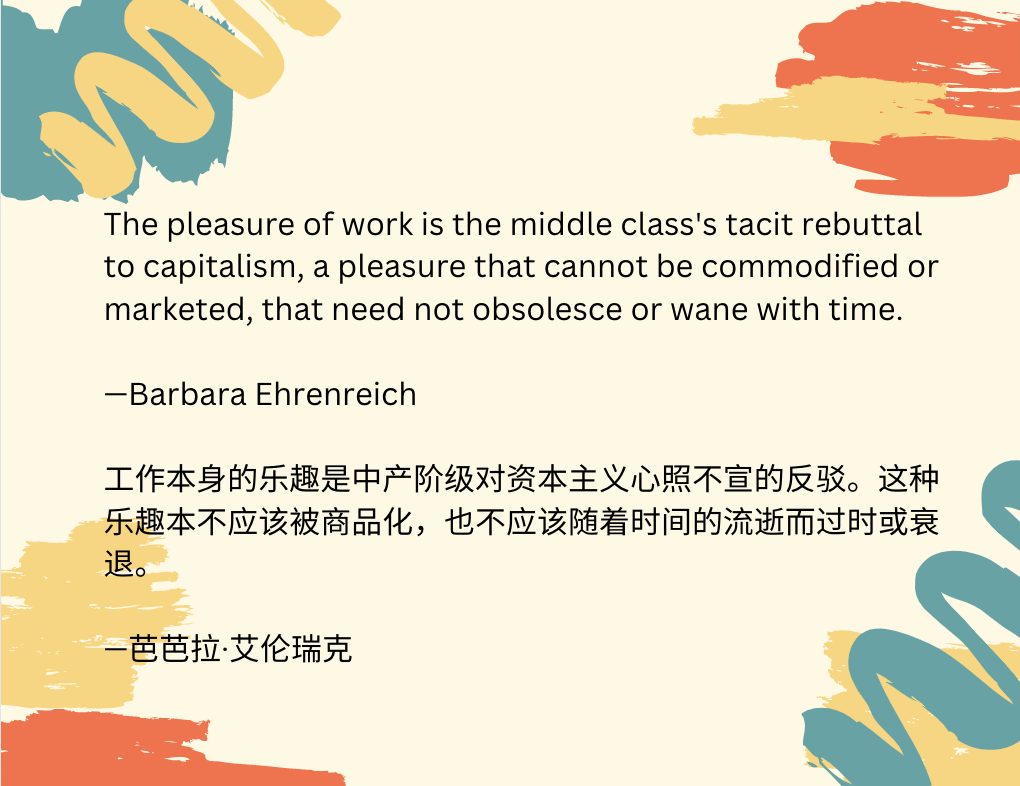翻译这篇文章,是想传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父权制下,女性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妈的!”
作者:梅根·墨菲
原文出自文集:Freedom Fallacy: The Limits Of Liberal Feminism
毫无疑问,“女人的选择”是女权主义话语的核心原则。为女性创造真正的选择,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狭隘范围内的选择幻觉,是女权运动的一个核心且合理的目标。但我们在过去 20 年中看到的,却是从这个概念演变而来的是一种不同的野兽。
“我要做我想做的,去他妈的!” 被认为是美国90 年代的女权主义“标志”,一些人认为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开始。这种口号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年轻女性而言。想象一下你正在摆脱社会的枷锁,同时拥抱和拒绝限制性的、厌恶女性的标签,比如“荡妇”和“妓女”,你会感到非常有力量,就像比基尼杀手的主唱凯瑟琳汉娜 (Kathleen Hanna)所做的那样,她摆脱了她在她的表演中脱颖而出,露出写在她肚子上的“荡妇”一词。在汉娜 (Hanna) 之前,麦当娜 (Madonna) 在 80 年代以类似的方式成为某种女权主义偶像,拥抱“性感”的服装和意象。她被视为掌控了自己的性(sexuality)并利用女性气质获得权力的女性的代表。虽然这种对传统性别歧视或男性定义的意象和语言的特别使用方式可能会让女人感到暂时的解放,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回收”(recycle)“荡妇”一词来反抗女性被性化?这个答案就没有那么直接了。

2011 年,一名加拿大警官向多伦多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的学生建议,“女性应避免穿得像荡妇,以免受害”。这些评论引发了 2011 年 4 月 3 日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次“SlutWalk”游行。游行蔓延到世界各地如拉斯维加斯、墨尔本、博帕尔和圣保罗。 “SlutWalk”被誉为 Take Back the Night 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化身。 Ms. Magazine 的一位博主写了 2012 年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正是第三次浪潮的感觉——那种个人主义的赋权——让“荡妇漫步”在年轻女性中流行起来,”并补充说游行是“SlutWalk”不像 Take Back the Night 这样的反强奸集会:它在情感上不那么激烈,它更多的是为了奇观。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评价,但在涉及激进运动时,“受欢迎程度”和更轻松的信息并不一定“更好”。
游行似乎没有专注于攻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强奸文化,而是表演性的,并且优先考虑媒体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关注个体、个人的赋权观念和穿性感服装的“权利”——“我做我想做的,去他妈的!”这句口头禅占据了主导地位。只要女性选择被物化,哪怕是选择去迎合男性凝视的行为也能被当成是积极的事情。
没过多久,游行就开始将性产业宣传为赋予女性权力的个人选择,其中许多人积极倡导卖淫合法化。在纽约市,游行的特色是穿着内衣的钢管舞者,拉斯维加斯的“SlutWalk”创造了一个口号,将“性工作”描述为女性喜欢的东西:“荡妇不是外表,而是一种态度。”无论你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工作而享受性爱,这就不会是对暴力的邀请。“SlutWalk”对“选择”和个人赋权的关注抹去了女性做出“选择”的背景,尤其是关于她们“选择”在性行业工作或“自我物化”,无论是在脱衣舞俱乐部、Instagram 还是街头。
2011 年,华盛顿特区的“SlutWalk”组织者计划在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举办筹款活动。毕竟,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者聚集的地方。可以说,进一步巩固女性作为性感对象(甚至是为了男性的快乐)似乎很奇怪。当受到质疑时,组织者回应说:“这不是一个批判性质的运动,它涵盖了女性希望做出的所有选择。”
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此支持”女性的选择”,以至于我们无法再批评可能导致女性“选择”在脱衣舞俱乐部工作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当我们批判性行业时,我们不是在批评“女性的选择”,而是在挑战男性权力和男性选择物化和剥削女性以谋取私利的选择,以及未能为女性提供机会获得体面生活的经济现实。女性值得一个不涉及脱衣舞、卖淫或色情的生活的世界。
面对严重缺乏选择,“SlutWalk”只是在简单地重新构建对话。 “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如果我们能让女性(和整个社会)相信性行业可以赋予她们权力,如果一些女性个体声称她们喜欢脱衣舞娘或三陪的工作,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面对持续和恶毒的厌女、性骚扰、强奸文化、色情文化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自由女权主义和第三次浪潮似乎走了一条容易的路,关注“选择”和个人身份,而不是直面根源问题之所在:父权制。

选择是女权主义话语和行动的关键部分。比如,它是争取生殖权利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这关乎到选择我们是否想要生育以及选择我们想要的身体和生活的权利。这种选择过去是,现在也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影响我们获得授权和自主的能力,不仅在家庭和个人方面,而且在生活和社会的其他更公共的方面。
因此,“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坏概念。例如,女性有权选择是否要生育、结婚、上大学等,这些权利是女权主义运动取得的成果,不能轻视。曾经有一段时间,女性不能做这些事情。在一些地方,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生殖权也正在受到侵犯,而在其他地方,女性在婚姻方面的权利很少。联合国估计,有25亿女性生活在婚内强奸不是刑事犯罪的国家。即使还有很多需要斗争的地方,尽管在女权主义话语中“选择”的力量很大,但过度使用这个词似乎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甚至这个词已经开始削弱了女权主义运动,而不是增强了它。
现在,当“选择”被讨论时,它通常以个人选择而不是集体选择(和集体自由)的形式出现。好像“我的选择”不可能对世界上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产生影响。好像“一个女孩作出的选择”就可以消除任何合理的批评或对她所做选择的背景的质疑。这很明显是一种关闭对话的方式。如果没有对话和批评,女性主义将在哪里(将会走向何方)?我们本应可以在不羞辱女性的情况下批评具体一些女性的选择。如果我们要理解和挑战影响我们选择的更大的权力系统,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思考我们的选择。
许多评论家确实将这种“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口头禅视为第三次浪潮和“后女权主义”话语的一个弱点;虽然这种态度并不普遍适用于整个浪潮,但它似乎确实建立了相当大的势头。仅仅因为我们选择它,任何事物都算作“女权主义者”吗?
虽然为自己做出选择无疑是一种赋权,虽然我永远不会反对女性选择穿高跟鞋、在婚姻中随夫姓、甚至出卖性服务的权利,但女人可以或确实做出这种选择并不等同于“女权主义”。为自己做出选择——无论它让我们感觉多么好、多么强大或多么满足——并不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女性的权利或地位,也不会反抗父权制。感觉良好固然很好,但这并不构成政治变革。换句话说,女权主义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本自助书。
性别歧视被定义为“基于一个人的性或性别的偏见或歧视”,但这个定义遗漏了一个关键方面:系统性权力。如果性别歧视仅仅是关于性别偏见,那么从理论上讲,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与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一个同等的问题。但是父权制度创造了一个拥有系统性和个人权力的主导群体(男性),他们压迫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女性),创造了一个使女性作为一个阶级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的制度。如果不承认父权制是性别歧视的基础,我们就只能采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性别歧视和女性解放的方式,即在个案的基础上评估歧视,纯粹根据个人的感受和经验,而不考虑男性权力的更广泛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背景——一个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压迫和暴力的历史——性别歧视就不会作为一个概念存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脱离这种背景的个人选择并不等同于女权主义行为。除此之外,对个人选择的迷恋实际上抹杀了这种背景以及父权制是一种权力体系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任何女人的选择(比如说隆胸手术)都是女权主义,那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选择背后的背景——物化、身体仇恨、资本主义、色情文化——所有助长对女性整体压迫的事情。
对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来说,如果女性做出的任何选择被视为解放或“女权主义”,她甚至可以“选择”支持这两种制度,没有人有权挑战她。在“选择女权主义”中,如果一个女人“选择”制作色情作品,这会助长压迫和物化,不仅是对色情片中表演的女性的物化,而且是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压迫和物化,并且有助于亿万美元的色情业。很遗憾的事,她仍认为自己被赋予了选择这条路的权力是好事儿,她甚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再然后,色情片也能成为女权主义。
著名的滑稽表演者蒂塔·冯·提斯 (Dita Von Teese) 在为那些称她的行为剥夺了女性权力的批评者辩护时说:“当我在上面表演 7 分钟,赚了 2 万美元,这怎么会让人失去权力呢?我觉得自己很强大。” 这句话体现了当今“选择女权主义”的问题,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赋予个人“权力”。除此之外,如果金钱是我们决定什么赋予女性权力和什么不赋予女性权力的主要依据,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与一个对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剥削和压迫负责的制度勾结在一起。如果女性通过物化身体或性行为获得补偿,那实际上并没有挑战物化和剥削背后的性别歧视观念。尽管 Von Teese 可以多买几双 Louboutins高跟鞋,但我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

“选择”以及它诞生的女权主义背景,已经被主流制度和自由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收,并被他们所利用。那些对女权主义或结束性别压迫没有特别兴趣的人现在正在告诉我们选择和自由是什么样的。这些系统告诉我们激进、革命或女权主义甚至是不好的。如果我们要求太多或错误的自由和赋权,我们就会被指责和攻击。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他们的选择版本,并告诉我们赋权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获得——只是要令人愉快的,性感的。而且,嘿,你猜怎么着!我们甚至不再需要女权运动了!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自我物化,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在上面贴上“赋权”的标签,瞬间就成了自由,其他人都需要闭嘴,因为“这是一个选择”。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女权主义是关于抵制父权制,而不是仅仅是加入其中。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可以像男人一样以压迫的方式行事就能“获胜”。当我们争辩说无论有没有我们都会发生性别歧视,所以我们不妨参与并充分利用它,或者如果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获利,这将以某种方式消除性别歧视。向父权制提出根本挑战不仅仅是顺其自然,《狂野女孩》的制作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自由是什么样子。一个女人从脱衣舞表演中变得富有,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解放。
没有政治或理论支持的选择是没有力量的。以牺牲他人(尤其是边缘化群体)为代价的“选择”并不激进,也不会促进平等。例如,“选择”物化我们自己,这并不是我们第二波姐妹们争取“选择权”的意思。通过选择赋权从来都不是针对个别女性,而是针对大规模赋权,以及让所有边缘化人群免受压迫的自由。
对“支持女性选择”的关注有时让人恐惧,因为这些支持扼杀了批判性思维。 我们已经将“批评”(critique)变成了“判断”(judgement),迫使我们将政治与个人分开。 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风险是巨大的:我们失去了对抗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的能力,并且继续不得不在一个不断将女性视为次等人的系统中生存。
个人主义支持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对集体斗争、社会安全网和服务以及更普遍的穷人和边缘化人群造成严重破坏。 作为女权主义者,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并结束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这一全球流行病,我们就需要超越个人主义话语,关注集体赋权,以应对这种日益去政治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