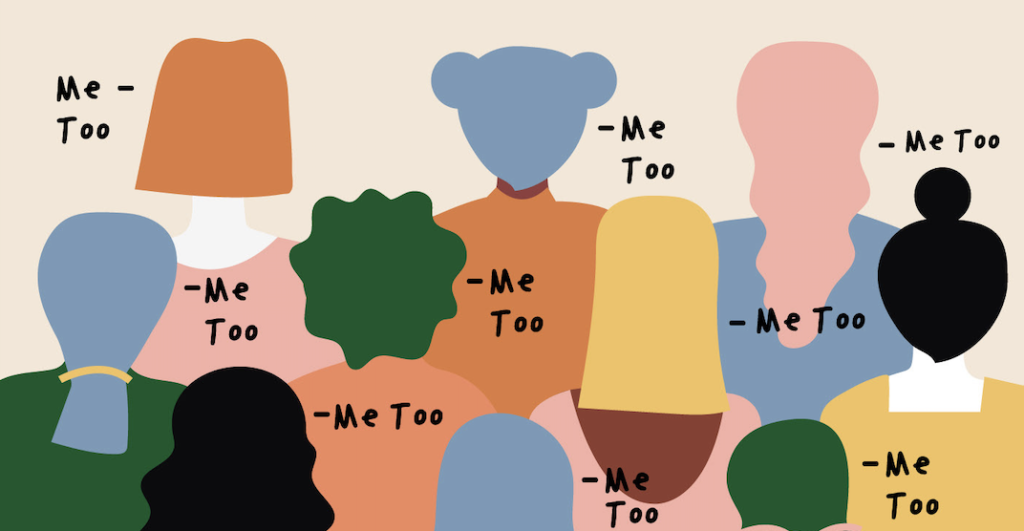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什么可以实实在在帮助弱势群体或者女性群体的事儿可以做?
每一个弱势群体里都有女性,而女性往往在这个弱势群体里更弱势,所以我个人重点放在女性身上。我的行为更多是在思想启发层面,一是受环境所限,二是它确实有效。
- 在社交媒体转发女权相关文章:语言是有力量的,社交媒体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传播工具。所以我经常在朋友圈,微博转发一些女性权益相关的文章并作出评论,久而久之,一些女性朋友会被触动,会产生思考,甚至来和我讨论相关话题。我不知道她们在思想转变以后会在生活中如何实践,但是思想转变总是第一步不是吗?
- ⻅缝插针鼓励女性自强:因为树立了一个关注女性权益的形象,常常会有女性朋友来跟我聊聊天。特别是聊到一些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而困扰她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会首先指出这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她没有问题。在冲突产生的时候,归因是很重要的一环。很多女性备受摧残最后归因到自己不够好,那就是拿起剑向内刺,实际上谁伤害我们我们就应该归因到谁头上。归因的下一步是反抗还是逃离,取决于个人的环境。
- 女权出柜,关照自己:声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在简中世界还没有被常态化,我们希望它可以更常态化,让大家都开始关注女性权益问题。而另一方面,每一位女性都或多或少在父权的泥潭中挣扎,所以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要关照好自己。毕竟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帮助女性。
—Ling
我生命中最亲近的女性就是我的母亲。提到帮助女性,我想到的就是母亲。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助她分担家务,陪她聊天。
我的母亲早早与我父亲情感破裂,独自一人抚养我长大。她或许文化水平不高,讲不出独立之价值当她身体力行的独自一人挣钱养家抚养我长大,放弃了许多属于自己的人生,她把独立的精神传给了我,独立就有了意义。
这些疲于奔命的独立女人,没时间哭诉。就算我们的社会偶尔注意到她们了,又何曾注意的是她们的困难呢?目的大多数是为了歌颂她们的伟大,往往也就止步于赞扬她们的牺牲。而这个现象,或许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探讨。
—蕉绿
帮助任何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倾听可能是一个可以去尝试或者努力的方面。有时候帮助是一次性的,例如在一个人陷入沼泽的时候递出一根木枝将他拉离险境;但有时候帮助并不是一次性,而是一个过程。人不是机器,不是在需要维护的时候涂一次润滑油可以再运转几个月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维护。每个人有自己的情绪行为和生活方式,每个人每时每刻有自己的特殊处境,每个人在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下有独特的需求。究竟怎么样帮助别人取决于被帮助的人的需求。确实帮助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一个怀有美好心灵的帮助者也会从助人为乐中找到快乐和满足,但更重要的是被帮助的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通过不断地倾听去抚摸需要帮助的人的内心和促进他们在所处的社会中的生活。有的时候,你在那里,在需要寻求帮助的人心里能种植下一份信任和支持,那已经是很大的帮助。每一个你和我,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面临艰难,面临需要被帮助的时刻,面临渴求有一团暖火可以驱散寒冷。每一个的你和我可能也没法去承担起别人生活和生命的责任,后者去努力生起那团火会有压力,但其实我们只需要伸出一双温柔的手,用自己的体温焐去严寒,每个人一点点温度,如果我们有很多双手一起来焐热弱势群体们的手,他们就会温暖起来。即使最需要被帮助的人,他们本身也是生命的奇迹,倾听支持焐热他们的双手会给他们力量激发出来他们的生命的能量,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目光陪伴他们走上他们自己的更好地人生之路。
—大盆
教育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对于经济独立又有余力的朋友,这里我推荐一个点对点直接资助儿童上学的网站:感恩中国http://www.owecn.com 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关注其他有政府监管的公益组织,不过也想说说为什么我信任这个个人网站。
通过这个网站,几年前我们家匹配上了两个藏族女孩,之后每年我们捐助的学费、生活费都会被直接汇到她们所在的学校。再由学校将生活费转交给她们。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助学款被女童家庭克扣的可能。女孩的老师偶尔也会发来照片、甚至视频通话告知我们女孩们的近况,所以可以确定她们确实是一直在读书的。即使真的要细究,我们虽然不能保证她们的生活费完全没有被其家庭克扣,但是如果她们家里有其他生活困难的孩子,我们也不介意被一部分钱被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哪怕是给他们家里的男孩子。因为我们可以确认女童的教育至少得到了保障。
—Simone
大学课堂上听到美国约40%的(15到59岁)的人会感染HPV,且95%的宫颈癌是由HPV导致的。深感震惊的我下课就去学校的诊所打了HPV疫苗。十年前很多人还不了解HPV疫苗,我把这件事分享给身边亲近的女生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不太熟悉的女孩也来问我关于打HPV疫苗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她们对我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会就她们最困扰的问题来询问我一个陌生人的意见。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帮助女性可以从身边,从很小的举动着手。一条小小信息的分享,焉知不是一件有益于一个女孩一生的大事。
从那以后,我很乐于和身边的女性聊关于女性健康的问题,看妇科医生有哪些注意事项,妇科体检需要做什么,有哪些短效和长效的避孕手段和各自的优缺点 ,到什么年纪需要做哪些筛查…… 随着年纪增长,我也遇到越来越多愿意互助的女性,不论是一对一的还是通过组织或参与活动和互助团体,自发地向他人提供关于心理健康,情感,和职场方面的帮助。
在帮助女性和弱势群体的议题上,我的观点非常实用主义。我认为帮助女性,并不见得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用政策和社会运动推动围观层面上的改变;不见得需要统一形式和内容,或追求单一的目标。草根式的,哪怕只是在自己的社交圈内部做一些尝试,也很重要。再者,我十分厌恶在做这些社会运动时参杂表演性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George Floyd事件期间,我的一位黑人朋友和我分享,她对于她的非黑人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分享参与游行照片的感到反感,因为其中一些人在生活中会时常发表一些带有种族偏见的言论。与其(只)在社交媒体上摆pose,不如照顾一次女性或弱势群体的生意,或倾听身边一个属于弱势群体的朋友的故事。这种贯穿在生活中的平权意识和小小的善意,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 喜欢待在山里林子里水里,大概上辈子是只海獭的Kaylee
我帮助各种弱势群体是出于某个模糊但自私的目的。这个目的可能是,我想通过我自己微弱的行为去消解个人对于现代生活的失落感。悲观的来说,在女性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声音逐渐被消减的今天,每个普通人都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工具”,一个让弱势群体们有自由有尊严活下去的“工具”。
我第一次有意识去寻找可以帮助弱势的工具是在大概十年前。当时我身边的人我的父母的工具是小额捐款。人祸捐一千,天灾捐两千。可惜我那时是个穷学生,没什么本金去做这件好事,有点钱也画在自己专业的材料费上。我算了算,到今天为止我尝试的不同“工具”中,有两个是我实践下来还算踏实的工具。
第一个工具:设计
第一次在用这玩意儿当成一个“工具”,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的。学校需要宣传材料,我被顶上去做海报,后来逐渐我自己开始有能力去号召大家开展关于女性设计师或者关注亚裔设计师的讲座的时候。我的设计海报的能力还得到了一些校外的人的喜爱。逐渐从那时开始,我开始义务为一些群体做设计做海报logo等等graphic design,有的是可以广泛传播的,有的不行。这毕竟是一个人人小红书或者Instagram的时代,图片作为一个更能直观更有时间效率的传播方式,无论观点如何的现代年轻人都逃离不了被图片填满眼球的现实。
第二个工具:算命
对,你没看错,就是算命。作为一个主要算命业余搞设计的家伙,无论是紫微斗数还是塔罗牌,八字生辰到六爻,有的是自学有的是老师教的。学习这些东西的初衷也是很简单,就是我想知道人类社会还有没有未来,开玩笑的哈哈。想学算命的人大多数还不是被“我的crush喜不喜欢我“这个宇宙终极问题所启蒙的。当建立起一定的credentials后,我从帮朋友亲戚算,到帮朋友的朋友甚至陌生人去算。一开始的试试水,到后来以捐款证明作为支付方法。让想了解自己命运的人通过选择任意慈善机构的方法,为他人也为自己积点德。这方式可能听起来很猎奇很好笑。但是,如果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他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更能共情哪一类型弱势群体,也不惜我神叨叨的做出这些福德。
当然,这世界上不止有这两种简单的工具。我常常在想,万一哪天我也变成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我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安全网能在我坠入谷底之时救救我。anyway,这些话讲了多了多少有点宏大叙述的嫌疑,听上去空荡荡。姐妹们!现在!就现在!打开手机找个良善的组织捐款去!
—智子
作为一个职场人,其实是经常感受到女性在职场里就是妥妥的弱势群体,尤其是30+的未婚未孕女性。当然这个不是短期也不是某个体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就尽可能在日常中,尽自己所能把女性拉起来或是把女性送上去。在职场里高层女性越多,女性的生存空间就会越好。
1、学会相信自己
一定要坚定的相信自己,只有你自己先相信你自己,别人才可能会相信你。在我的观察里,出现同样的错误,女性同事往往会更在意这个错误本身,然后消耗大量的精力在反思自己的错误上面。这不仅影响自己的情绪,甚至有时候会让自己陷入自我怀疑。
其实大可不必,出现问题,总结、复盘、优化,继续推进就可以了。在职场里面过多的情绪消耗对成长没有帮助的。有困难是正常的,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没有人的能力是完美的,一定要时刻相信自己。
2、鼓励女性向上社交,争取更多的机会。
职场里除了要埋头做事,也要积极的向上沟通,大方的展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在中国这个社会,用人唯亲是不变的铁律,要掌握被领导信任的能力。因为信任是职场里面被「重用」的唯一标准。
3、在客观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把资源和机会倾斜给女性。
在我的团队里面,男女比例差不多是1比1,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把机会留给女性,第一是我发现期时女性在人际沟通、细节把控、流程跟盯上其实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些特别需要注意这几方面的工作交给女性会让人更放心。女性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放大它。
第二是让女性在职场里面获得更多的机会表现自己,也是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机会,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中展示出其专业性,越有可能消除职场偏见。
—跳跳
如何低成本留学北美?
美加的STEM领域有很多硕士项目,这些项目不少是可以提供助教奖学金(teaching assistantship)。助教是一份每周20小时的工作,免学费,并且还有一份(不高)的工资。这个恐怕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往往只盯着排名,其实在北美找工作或者申请博士,毕业学校排名并没有那么重要。硕士一般只是一两年,如果有助教奖学金的话,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跳板。而且STEM专业提供很多基础课,所以不论是什么学校,都有比较多的教学任务,也就是说有招收研究生来做助教的需求。更何况美加有非常多的高校,所以拿到助教奖学金来留学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对文科不了解,但是理工科的确能够打开非常多的大门。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尽量学理工。我曾经认识一个女生,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计算机。她读了两年后就申请出国读计算机专业了。但是几年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专攻油画了。不但不再编程,连电子邮箱都没有。她说她选大学入学选计算机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容易出国,为了出国学艺术。
豆瓣上有个women in tech小组,里面大部分的讨论都是如何转码,如何申请计算机专业。然而另外还有很多STEM专业(比如数学,统计,数据科学)其实比计算机好申请,更容易有助教奖学金,之后在北美也很好找工作。国内如果学过高数,基本的统计课,就可以满足很多学校的申请要求了,绩点高的话在这些学校拿到助教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只盯着排名来申请。
STEM专业毕业出来,除了去知名大厂做码农也是有很多选择的。比如生物技术(biotech)领域需要大量做数据分析的员工,需要生物学生物工程相关的专业人员,药厂需要有统计背景的员工,咨询公司需要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以便与生物技术公司合作,甚至棒球队,橄榄球队都需要会做数据分析的员工来分析球员表现,球队策略。
大家在读研时可以尽早开始了解不同行业招聘的要求,同时积累科研或者实习经验,可以和教授做课题,也可以暑假时在校外找实习。这些经验不管是之后找工作还是读博都会很有帮助的。有些行业可能需要你学习一些其它领域的知识,比如你可能是计算机或者数学背景,但是多学一点生物学就可能帮你在生物技术公司里找到更好的机会。
即使是在北美,STEM也是性别比例失衡的重灾区。所以北美的学校,不论排名,在招生上一般来说都是有着平衡性别比,特别扶持女性及其她少数群体的道义上的责任的。对女性的打压遍布全世界,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结果自己就先把自己否定了。招人的时候常常发现,女性申请人普遍条件好,准备认真,而男性申请人非常参差不齐,有时简直令人迷惑,他究竟是怎么觉得自己合格的?所以姐妹们,不要轻易给自己下断言,可能的话多申请几个学校,不同梯度的都申请至少一两个,先申请了再说。
—Aud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