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Fear of Falling。在这本书中,作者Barbara Ehrenreich深度剖析了二战之后蓬勃发展的美国中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职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虽说作者是站在1989年回顾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进程,但是了解这一历史进程,无论对于认识美国当今的政治经纬,还是认识其女权运动的特殊社会背景来说都有着独特的价值。不仅如此,对比中国这样刚刚形成规模庞大且日渐焦虑的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可以看到很多平行的故事。

书里面谈到了一点美国的女权主义。作者讲述了美国女权运动最初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美国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并不是无源之水,也不只是一些人单纯地在象牙塔里琢磨出来的理论,它有着丰富的社会背景。特殊的社会背景既引导了那场运动的方向,也导致了其局限性。
之前这个公众号也有发表过各种对于当代女权运动的思考。我想,对于今天想要推进女性解放事业的人们来说,回应时代背景中最强烈的呼声才能最有效地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同时也要注意着那些鲜有呼声的地方所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矛盾。
————————————————————————————————————————
Barbara Ehrenreich首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即美国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主要是中产阶级自我意识演变的一部分。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对于美国的劳工阶级来说,男人和女人大多数的出路就是以后找一个体力活儿来挣钱。只不过传统上男性更容易从事建筑业、重工业之类的重体力活,而女性更多从事诸如接线员、打字员、服务员这种轻体力活或者婚后成为家庭主妇,但这个阶层中的男女对于接受教育以及参加体力劳动的期待是差不多的。
不过二战后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十分独特。虽然一个中产家庭中一般父母双方都经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但是男性一般会成为家里的唯一的working professional或者说唯一挣钱的人,而妻子却会和不少劳工阶级的女性一样,“选择”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这种安排非常特别,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只有美国在当时欣欣向荣的经济背景下也可以让一部分阶层实践。
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会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的近半数在家仅仅从事服务劳动。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甚至有美国的评论员担心,60%接受过通识法国文学、有机化学等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去当家庭主妇,会使得国家在面对让女大学生去修大坝、建水电站的前苏联时处于劣势。

而对于美国中产内部来说,这种安排还导致了几个棘手的问题:
首先,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全职做家庭主妇、带孩子,是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按照Betty Friedan在她的成名作The Feminine Mystique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有着良好教育背景、通常是心理咨询师、总裁、医生的妻子的人,虽然看似衣食无忧,却普遍有说不出的痛苦、不安、焦躁。和社会脱节或者不开心的女性,小孩儿也容易养出现性格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当一个富太太躺在钱上,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也许吧,但我们这里说的是躺不下去的中产。
这种困境很普遍,中产阶级女性意识到这种痛苦,也算是美国女权运动很重要的一个起点。(这种女权意识的觉醒只属于中产白人女性,虽然这一局限性常被拿来诟病,却也只因为Betty Friedan等女权先驱也仅有这个女性阶级的经历。毕竟,底层女性、黑人女性可能主要在和贫困、家庭暴力作斗争,确实关注的问题和她们不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孩子的教育。中产阶级不光在乎人口的再生产,也比其他任何阶级都更在乎阶级的再生产:他们不光得能把小孩生出来养大,还希望能保证小孩以后的阶级。至少不比他们现在低,能比自己高一些就更好了。这一方面就首先对小孩的成长环境有了更很严格的要求:按照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语,就是大家很在乎下一代能否传承所谓的“中产阶级精神”(middle-class ethos)。

“中产阶级精神”往往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需要对消费主义是认可的,不能小小年纪就躺平、无欲无求。至少也得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个大房子,希望以后能开一辆好车,希望自己对高消费标准是有一定热情、有追求的。另一方面呢?也不能见好东西就躺上去享受,还得学会延迟享受。经过十数年的教育(学徒)时间,最后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
这让家长也产生了很多焦虑,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有诸多矛盾:一方面一个“优秀”的孩子需要独立、有自己的创造力、主观能动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怕“动”的方向不对,给足自由、解放天性了以后反而小孩“不能吃苦”以及“找不到正确的路”了。中产阶级尤其容易焦虑,毕竟期望不小,却没有任何试错空间。
大家都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这可能意味着家庭需要有更高的收入,也就意味着希望女性最好也可以去工作。但是同时又不想把这个小孩就丢给一个“阶级更低”的人,例如保姆。当时的美国的社会思潮普遍认为“更低阶级”的保姆会通过溺爱孩子把孩子给惯坏。教育孩子的人要有更严格的训练,才能养出一个好孩子。这也逐渐导致女性既要承担家庭的任务,又要承担这个社会上的责任。同时,这种社会背景也给小孩来说造成了很多焦虑。作者认为,这种焦虑和美国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发现时代变了,自己没有办法像自己的父母那样“轻松”地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住着漂亮的大房子,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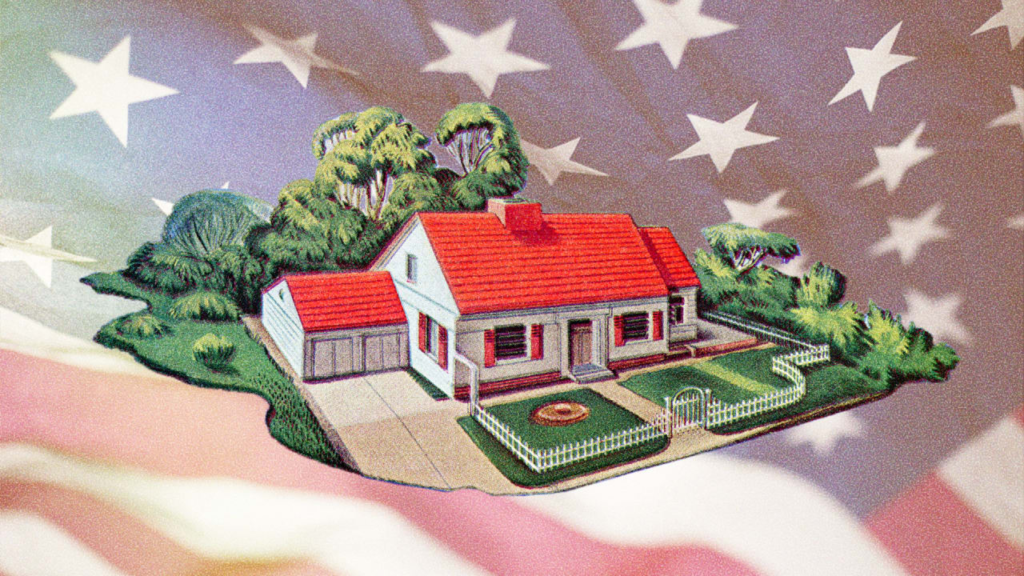
————————————————————————————————————————
写到这道,突然想到,女权在中国虽然土壤不一样,但是也有那么一点可以类比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条件普遍不好,也缺劳动力,壮年男性和女性在“是否参加社会劳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期待是一样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有点像美国60年代的底层阶级。
现在,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希望更多的女性参与工作。但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后,并且可能确实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社会的刻板印象是觉得全职太太是一个很幸福,很显示自己阶级的象征。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现在的中产有点像在复刻美国60年代的家庭主妇焦虑和后来的中产焦虑,包括养娃的焦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地区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男女矛盾表面上看更加厉害了,但是事实上则是,女性受高等教育后,女性意识觉醒的必然。这个时候不管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还是听上去更洋气的“全职太太“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最优的选择。
这么对比一下,我们也容易意识到,各个阶级的女性都面临着根植于自身所在阶级的困境。如果说底层女性面临的主要是人口再生产(养育后代)的压力,那么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则是阶级再生产(教育后代)的压力。
因此,我们不能将“全职太太”这种与传统窠臼相比换汤不换药的模式视为应对社会再生产困难的理想答案,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产阶级转嫁到其中女性身上的阶级再生产压力是全体女性面临的困难的全部本质。这既提醒我们不能将“找妈妈带孩子”或者“请保姆”视为完全解决女性困境的简单方案(在许多情况下这不过是将中产女性的压力转嫁到了其他女性身上),也提醒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不同阶级女性(尤其是那些在媒体与舆论中缺位的那些她们)所面临挑战的不同性质。

比如说城市当中的女性,其实很多时候更多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要在职场发展的时候受到阻碍,也能希望职场家庭两不误。一方面,如果组建家庭的话,需要足够的时间能养孩子;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因为完成对社会再生产这种重要的任务,而在职场中受到惩罚,丈夫也别做甩手掌柜。但是对于劳工阶级来,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劳动待遇的改善,说白了就是摆脱“贫穷”大概远比其他的重要。这里也真的写不了什么,因为真正的穷人,总是很遗憾地被系统地忽略了。
写到这,不知道怎么结尾。我最近总觉得,普通人的阶级焦虑总是会有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焦虑的时候,就多把时间花在学习、工作、保重身体上,毕竟这些是短期就能见效的事儿。一定要上个价值的话,呼吁动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缓解不同阶级面临的各种病态压力,也是女性赋能很重要的一环。
